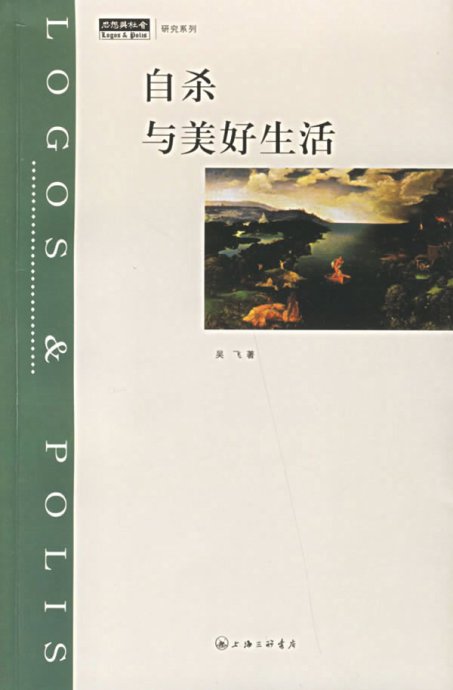
吴飞著作:自杀与美好生活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南方传媒研究》。
随着深圳富士康12人连续跳楼事件的发生,自杀,第一次作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人们发现,并不仅仅是城市的自杀现象怵目惊心,农村更是长期以来自杀频仍之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底是哪些生命与生活观念、生命与生活状态促成这一悲哀的现象?回到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中,或许能寻到点解释的蛛丝马迹——虽然它极可能是理性的狂妄。
每个社会都有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些人生取向,在前现代的西方社会,无数宗教徒把死后的永生作为最重要的人生取向,这也就成为那些社会的主流共识。
与西方现代性成功及其单向度生存状态已基本改观不同,百年以降,中国经历了传统崩溃与现代性流产双重失败的同时,传统与现代生存方式中那些不良因素却被牢牢吸附于这个社会进程的每一个阶段。
前三十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它依靠官民与城乡这两把大剪刀支撑一个官僚帝国。当这个烂摊子再也支撑不下去之后,所谓的改革开放才开始,而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究其实质而言,与前三十年相比无非是剥夺之后不让吃饭和一边剥夺一边让吃自己的饭的差别。
在政治领域,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改革。公权力不受监督与限制,公权力缺乏分立和制衡,公权力缺乏竞争性选择等一系列最需要的基本政治改革,至今似乎遥遥无期。
于是,国人在逐步进入多元化人生取向的同时,主流的人生取向集中于摆脱生活的贫困状态,除了经济生活存在一定自由空间,其他的公共领域生活步履维艰,从而形成了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及其派生的伦理观。这套价值观和伦理观,使得社会在评价和接受一个人的时候,以人的财产多寡为标准,而不是以正常社会通常推崇的真善美为标准,从价值序列中,它没有能处于最高位阶,而是处于从属的虽非完全无用却次要的位置。那些真心侍奉真善美愛的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尤其能感受到孤独与压力——虽然他们也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和鼓励。
这种情形下,人们的生活也就被很单一的评价体系所匡限,出身、地域、职业、性别、长相、能力、性格……所有一切似乎都因金钱的裹挟而被进行三六九等地等级化划分。
举国变成了金元帝国,爬上权力高位的目的是拿权换钱,有钱人拿钱换权的目的还是钱,色相用来换钱,就连感情也可用来换钱。为了钱,无数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违背底线良心与道德,黑砖窑、毒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假疫苗、假药、假保健品……,这些非公权力性质却怵目惊心的社会腐败现象,确实说明这个社会为了钱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已经溃烂至骨,几无可救之药。
于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国民待遇差异难以改变,广大农村人口生活比原先有所改进之处,只是2006年之后不需要交农业税了,而这在GDP中占有的分量本来就微不足道,以及农村医保有所推进,但对于一直就没有保障的农民们来说,这点进步远不足以让他们有生活的基本安全感,而相对于肥得流油的政府,更是杯水车薪。
当国有普通企业经营不下去时,大量城市失业人群就被抛入一望无际的无保障之中;当民间经济在税负重压下难以发展的时候,从业者的待遇也不可能改进;由于独立工会被禁止,外资企业原先所享有的优惠政策也没有给工人们带来优惠,取消优惠后状态更不可能改变;只有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才能让他们的员工分享一点垄断利益。毫无疑问,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极度畸形和变态的市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城乡人口的限制性流动在使得城乡差异减小的同时,也使得城市平民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但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产业工人,在与城市平民的生存竞争中依然身处劣势,并且以更为直观和残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由此可见,金钱崇拜的现状,有其现实的生存根源,正是这一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状态,决定了当代中国人生存的艰难。当官贵豪门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时候,千千万万的城市平民诅咒房价居高不下而沸反盈网;而此时,还有千千万万没有时间上网、没有条件上网的人却挣扎在生存线上,为每天的三餐一宿奋力拼搏;至于许多贫穷的农村,则还有无数人奄奄待毙于半饥饿的贫病状态中。
当一个社会只有极少数人享有比较完整的生活保障时,当绝大部分人,无论是否富裕,都处在缺乏制度保障的不安全感之中时,金钱拜物教成为社会主流人生取向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这个民族的超越性信仰原本就极为稀薄,古代的官本位到现当代不但没有任何减弱趋势,甚至变本加厉、杠头开花,有权就有了一切的现象比古代更为严重。尤其是权力与暴力共存的生活环境,对人心的荼毒更需关注。
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权力—暴力”崇拜,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仇恨教育与暴力示范,践踏尊严、宣扬残忍等血腥场面的公众观摩,教科书、影视艺术对上述观念的肯定和宣传,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观念系统,而愛的教育、人道精神、非暴力的和平理念则濒于灭顶。公权力及其盲从者以强力甚至暴力的野蛮血腥手段,将本该多元共容与共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强行铸造为群体的一元化和个体的单子化,破坏甚至粉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正常情感。
于是,被剥夺灵魂的国人在一望无际的情感废墟上生死辗转,失去真善美的信念,失去希望,失去愛。全社会被暴力文化催眠,浸淫于暴戾的社会氛围不自知,从而形成畸形和危险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其基本特征便是 “恶的庸常化”,即在正常社会里被伦常观念否定的行为方式,在“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中却得到合法性认证与正当性鼓励。
当前30年暴力破坏情感及其各类苦难被刻意回避,原有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因此未能理性消除,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权力—暴力”社会观依然一统天下,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继续以“权力—暴力”模式,控制社会资源,剥夺千千万万人正当的生活权利,以暴力拆迁、司法不公为典型标志的公权暴行,几乎彻底撕掉了遮羞布,以另一种怵目惊心的蛮横在人们心中烙下一个个新的血痕。这带着血腥味的权力、财富、地位等偶像招摇过市,旁若无人,迎来许多人既痛恨又膜拜、既妒忌又欣羡而流着口水的目光。
于是,贫富分化以及“权力—权利”严重不公的巨大落差,替代了改革前“奴役的平等”,公权滥施暴力引发的愤懑、嫉妒、怨恨、无望等转型焦虑无所不在,形成以“非平等奴役”为特性的第二期“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成为新的社会特征。
持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虽然废除已经100年了,但科举制导致的官本位制及其因此而来的权暴文化并未有多大改观,不但没什么改观,甚至因为科举制的废除及选官制度的党治与人治特性,而更加远离真正的文化与文明。古典时代的文雅艺术,被新时代无情摧毁,而流氓无产者那些粗俗无文的痞子文化占据国家主流审美地位至今。
这种痞子文化带来的除了官场权斗本身的极限无耻之外,还带来权贵们生活的糜烂与粗俗,其本质是除了权斗之外毫无生命迹象的空虚,同时,如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权贵生活方式会大规模地影响民间生活方式,成为民间的效仿对象。庸俗唯物主义的生活哲学于是遍布全国。
除此之外,倘若日常生活中经常性地亲历、听闻、宣说残忍的荼毒人命事件,暴力与仇恨以及对生命的践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的心理底线就会被不断地无限度突破,久而久之,蔑视生命的状态就会潜伏在心中,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残忍对待自己或他者的生命就不足为奇。
城市产业工人,倘若都生活在一个把人严重甚至彻底机械化、螺丝钉化的工业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无暇交友,无暇恋愛,只有永不停止的劳动,并且工作毫无独特性和创造性,可以随时被替换,收入低下,自身的脱困以及改变家庭经济状况都变得遥遥无期时,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便应势而生。
农村农民,倘若难以改变贫困现状,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家庭尊重,“贫贱夫妻百事哀”不算,还三天两头吵架,大家庭里,婆媳、翁婿关系紧张,缺乏温柔的愛情、友情与亲情,这生活又有多少乐趣?
被官府欺压迫害无处申冤和活不下去的人们,倘若面对自己顷刻间变成灰烬与瓦砾的家园,无以救济,无力反抗,这生活于他们是否还能继续?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生活状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比比皆是,暴戾而单向度。
在数量庞大的自杀事件中,到底有多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有多少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有多少是抑郁症导致的?这些目前尚无较为精确的统计,而且可能也永远无法统计。
400年前的1600年左右,在中国做传教士的利玛窦先生,曾在其《中国札记》中有过这么一段话:
“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是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怯懦地只为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细小的事自杀。” 。(《利玛窦中国札记》页92—93,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一版)
北大哲学系教授吴飞先生在其《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第一版)中说到,中国农村许多人的自杀,其实只是“气性太大”,尤其是夫妻间吵架导致的随机性喝农药,救得晚就死了。这“气性很大”恰恰与利玛窦所谓“他们往往为了很细小的事自杀”相互印证,他在另一本自杀学专著《浮生取义》中有一张农村人部分自杀统计中所列举的自杀原因,更是说明这种独特的中国式自杀的普遍性。
如吴飞教授所言,现代西方自杀学遇到这种现象只能目瞪口呆,他们无法解释。涂尔干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利己型、利他型、反常型,即使按照这一分类,上述中国式自杀也难以归到涂尔干所说的反常型自杀里。然而,正如加缪所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述中国式自杀现象依然有它自身独特的哲学意义,生命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消灭,难道还不够哲学?一定程度上说,既然说出“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句话的苏格拉底,被认为是哲学家里的哲学家,那么因为“气性太大”而随意结束自己生命的现象更是哲学里的哲学问题。
但这种因“气性太大”而自杀的现象,看似荒谬,其实却有其本身的逻辑可循,并不是非理性的——一定程度上说,甚至十分理性!最多只是那一刻显得莫名其妙、非理性而已。
在庸俗唯物主义盛行的中国,人们普遍缺乏宗教信仰,甚至无数国人根本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这一生命观念使得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考量更多建立在现实生活状态本身的基础上,例如,生活水准高低、生活乐趣、情感(亲情、愛情、友情、婚情)饱满程度等,而更少形而上特征。这种形而上特性稀薄的现象,可能大大增加未经深思熟虑的触发性自杀型态。这些触发性自杀方式,看似未经深思熟虑,但它也是在长期的混沌中酝酿而成的,它包含着模糊的生命空虚与荒谬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以及不可预期性,就是当事人自己也常常没有明确而只有模糊的自杀意识,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是以非生命的态度对待生命问题。这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式自杀现象中非常普遍的形式,而且它连及历史,具有传统特性。
雨果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活着。问题是,对许多人而言,生才可怕,更可怕的是无法立刻就自然死亡。倘若一个人因了无生趣而对自己的生活总体评价是生不如死,那么其活下去依靠的不是基本的生活勇气,而是惯性与惰性,一旦某个令其感到生的乐趣与情的留恋彻底丧失的时候,这种触机而来的“气性”就可能导致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结束别人的生命。
连续的屠童刀虽砍弱者,实质是自杀;富士康的连续跳楼自尽,实质是模拟杀人。以当事人自性论,都是轻生蔑生;以环境的他性论,都是对这个时代不公、不平、不义以及生活中的不顺,使用了错误甚至罪恶手段的控诉与反抗。连续屠童案中自杀性的屠戮行为与连续跳楼的工人自杀并无本质区别,当然,伦理谴责与同情、法律惩罚,此二者与上述性质并不冲突。
王国维先生是否因“可愛”与“可信”的冲突而自沉于昆明湖已难以探知,但他有一阙著名的词,也许最准确地回答了中国式自杀问题:“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做连江点点萍。”
显然,这不仅仅是感悟者个人的私情,它也代表了中国历代社会的公议;不仅仅是纯粹的生命感悟,还是混杂了社会性的控诉;不是某个时代的特异感受,而是就中国历史的常态感慨。
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中国自杀人群,精确地了解其具体成因注定不可能,若要强为之,甚至反倒是理性的狂妄。自杀及其原因之无法被精确求证,正如生之神秘,如愛情之神秘,任何一个对生死抱有真正敬畏的人,恐怕都不会轻言他人自杀之具体原因,更不可能狂妄地以为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
生者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是尽己力让这个制度变得正常一些,让这世界、让人和人之间多一点温情,多一点善意,多一点真诚,多一点欢笑,以便那些清晰或混沌判定自己生之不必继续的人们还能增加一点点留恋的生趣,因为那也许同样随机性地激起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