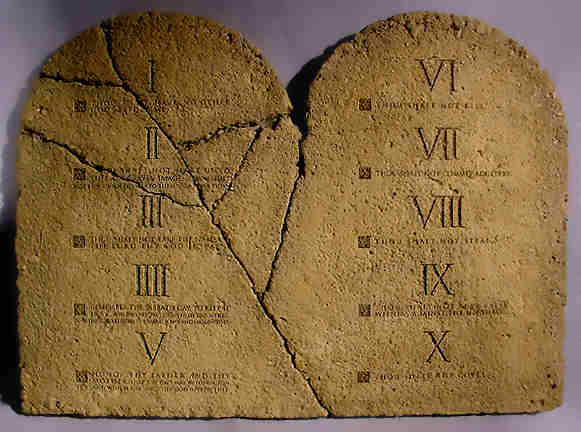
十诫
伦理:浮萍还是大树?
萧瀚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源于习俗,这很能代表希腊精神在道德哲学领域的见解——他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因为不服从习俗及由习俗来的伦理而被鸩杀。
比较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各自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是个平静的哲人,仿佛与世无争,却进入亚历山大大帝的宫廷并成为他的老师,而苏格拉底则因为做城邦的“牛氓”,到处挑衅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并且为了心中的神最终含笑饮鸩。
因同样被视为美德伦理学,有人试图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打通,牟宗三先生甚至致力于将孔子与康德打通——当然,通常而言,这是徒劳的。不说康德那样的伟大体系,就是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完整体系也是孔子不具备的。孔子的思想作为格言固然不错,但这种被黑格尔正确地嘲笑为“为了保护孔子的名声还不如不翻译”的毫无思辨能力、经不起追问的伦理格言,并不具有太大的学术思想价值,而历史更是早已证明,儒学作为一种伦理学说,落实到现实只有墙头草效果,千年依附权力,做权力附庸的历史已够说明问题。
康德讨论伦理有著名的三大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在他那里,离开了上帝伦理就无法存在,但因为理性有限,所以没法使用人类理性论证其存在;离开了灵魂不灭,也没有伦理——既然不承认灵魂,要伦理干嘛?离开了自由意志,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奴隶没有道德。道德需要理由,如果伦理仅仅是来源于习俗(且先不追问习俗来源于什么),那么表面上看来仅仅利人不利己的道德如何能长期稳定存在?
伦理学无非是要解决道德的理由问题。那么道德到底得有什么样的理由才能坚实如参天大树,而不是如随风浮萍?
将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到位的,最早的人是摩西。摩西带领尤太人出埃及,远离奴役,奔向自由——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关于文明的全人类的隐喻。摩西创立的以十诫为核心的尤太教,给人神关系、人人关系设定了基本的规范与界碑,明确了人对人的义务,是人对神的义务的结果,即人对他人的义务根本上源于履行义务者自身的内在需要,第一次给人类的伦理确立了最坚实的根基。
19、20世纪美国拉比考夫曼.科勒(K.Kohler)在其《尤太教的伦理基础》一书中说:“一旦与宗教分离,伦理本身就像一个破裂的蓄水池,盛不了一滴水。无论多么鲜美的果实,离开了茎和叶,都无法结果。你可以把良心比做一根指向正义和善的磁针,但请不要忘了,如果没有周围存在的巨大磁场,磁针是无法起作用的。”(转引自科亨《尤太教——一种生活之道》)这段比喻,十分形象地说出宗教与伦理之间地基与大厦的关系,当然,正如光有地基,没有大厦,这地基的价值也就有限,因此,尤太教除了强调信仰上帝的根本重要性之外,并不认为“因信称义”,而是“因行称义”,即信仰需要外在言行的表达才能得到确认,这是塔木德之所以会规定613种行为准则的原因。
在上述肯定宗教与伦理的根茎关系论述中,其实都省略了一个更重要和根本的问题,即一神信仰。在宗教与伦理的关系中,还涉及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差异问题,多神教是否也能成为伦理的根基?从许多现象来看,多神教能够部分地成为伦理的依据。多神信仰本质上只是人类将自身偶像化的产物,就是所谓 “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这与一神教“神不可有形象”的智慧不可同日而语。偶像化的、数量众多的神导致了伦理依据涣散而混乱,无法像一神教那样建立逻辑上一贯的伦理准则。这种混乱和涣散,有时甚至使人行为邪恶,从而成为人际纷争、族群纷争的根源。苏格拉底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而逐渐走向信仰独异于希腊众神的自己心中的神。至于各种一神教之间的冲突,则与它们各自反对偶像崇拜不彻底的教义本身有关,例如尤太教里的弥赛亚教义就给偶像崇拜留下空间;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将耶稣崇拜为神,也是偶像崇拜的后门;伊斯兰教虽然否定默罕默德是神,但将其视为最伟大的最后一位先知,并且供奉其生前一切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这与摩西死后连墓地都被隐去相比,远不及其智慧),这本身也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只要有偶像崇拜,就会有伦理冲突,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偶像崇拜也因彼岸与此岸的差异而有分别,一切偶像崇拜里,此岸偶像崇拜是最邪毒的伦理绝杀毒品。多神信仰因其一定程度的彼岸性特征,使得信仰者尚有抵御现世各自诱惑的超越性能力,比如万物有灵论对森林的保护就是一例。而此岸偶像崇拜,崇拜者们相互之间,除了物质性的权力、金钱、地位……等现世利益争端之外,就没有多少现世利益的抵御能力,此岸偶像崇拜者的伦理建立在物质性利益基础上,因此为了这些利益,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丧尽天良的事都不在话下,这就成为伦理的地狱。
另外,即使都是彻底的一神教信仰,只要制度上政教合一,那么冲突也不可避免,因为教权掌握者既掌握教权,又掌握政权,必然导致宗教不宽容,这是制度设计的问题,不是一神教一神信仰的问题。
不过,说一神信仰是伦理的基础,这不是理性单轨的产物,而是启示与理性的双重产物。在一神信仰中,最核心的伦理根源在于对神的人格性情感亲和,即马丁布伯从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理论(上帝、人、世界之间的三对关系)发展出来的“我与你”的关系。在一神信仰中,上帝是有生命的永生之神,不是如自然神论那样仅仅表现为一种自然法则,正如海舍尔在《觅人的上帝》中认为的,不能想象创造生命的上帝会没有生命,因此,只有信者所信仰的上帝是有情感的,信者才有可能从情感上接受启示真理,成为生活的依据,同时,经验和思考研究也给了理性以存身之地,使得信仰作为生活的依据更具有自省能力,从而不断自新自正。
西方文化中,信仰(启示)与理性一直是最重要的关系,双方相争相斗也相辅相成,但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它们很难总是处于均衡状态,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使得信仰迫害理性,而近现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则导致理性妄自尊大、蔑视信仰。其实,真正的理性是知道自己边界的理性——就是康德所划定的那条边界,而要自知边界,必须承认并深刻理解和接受启示真理这一超理性现象,如此理性才不可能狂妄地自以为无所不能。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试图以理性建立伦理学的尝试,至今未息,麦金太尔等当代思想家因深感启蒙运动以来伦理根基所受的戕害,而试图回归亚里士多德传统。这种努力值得敬佩,但仅仅以理性认知、逻辑论证,究其最深的根源也只是审美精神,其所建立的伦理学,只能产生辅助性的伦理结果,而无法成为现实伦理的终极来源,因为理性缺乏信仰所产生的情感温度。缺乏情感温度的伦理说教,无法成为人们言行的自愿结果。情感,只有情感,只有信仰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才能成为伦理最深刻而坚固的依据。
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儒家伦理观,且不说儒家伦理在其最初创建时的血缘氏族性这一先天缺陷,即使在经过孟子、子思、北宋五子、朱熹、阳明心学以来“上求神圣、下寻普世”的努力,依然无法建立稳固的伦理生活现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儒学伦理根基危浅,其危浅就在于缺乏像一神教那样存在一种对“有生命的终极神圣”的信仰,缺乏像一神信仰那样强烈的情感以及因此而来的强烈信念与坚定意志。朱熹之前,儒家“天”的概念虽有人格化成分,但也十分微弱,而朱熹则在回应佛家挑战过程中借道道家创建的新儒学,却将“天”进一步“理性化”,以至于被当时不少儒家视为“道家”。这成为阳明心学在此问题上突围的起点,但他的突围并不是回归向上的终极神圣并将其生命化,而是转而自求,这是路径的错误,其弊端显而易见:这种融汇了佛家思想的新儒学,虽然其有强烈的情感甚至意志,但由于其缺乏一神信仰那种内在的谦卑与感恩心理状态,其继承者、学说接受者最后沦为历史上嘲讽为满街狂禅的“王学末流”,也就毫不奇怪。至于阳明心学之后的儒学,无论在现实伦理效果上,还是学说本身,其实都没有本质性地超越前人,现当代新儒学之新,只是衣衫的光鲜,而不是内瓤的革命。
正是儒学的这些弊病,使得它在历史上一直只是权力的附庸,这种根基危浅的伦理学说,由于缺乏类似一神信仰的强烈情感和坚定信念,在权力和暴力的挤压之下,在现实物欲的诱惑之下,无法获得稳定的伦理生活力量(特例除外,因为永远会有例外)。伦理意义上,它只是一株随风的浮萍,追求的目标似乎显得很高蹈,一落到现实却柔弱得如残花败柳,这正是儒家人物伪君子倍出的根本原因。
22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通过其伦理学著作,试图帮助人们寻找建立幸福生活的方法,他的理论曾经产生巨大影响,至今未息。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西方真正建立伦理规则的,一直都是其一神信仰的宗教生活。
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基于一神信仰基础的强烈情感倾向,群体意义上的好的伦理生活就是流沙上的大厦,随时可能坍塌。自由民主宪政共和政治,作为制度本身也绝不是永恒的,无论起点,还是终点,若无支持这种政治的生命性一神信仰基础上的伦理生活,也是不可持续的。
2011年6月15日於追遠堂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